第三节 罗浮的起源
1. 漂移的山
不同于罗浮山脉的浮山,大部分漂浮的山一直都位于原地,人们之所以称呼他们为漂浮的山是因为这些山的浮水线会变化,而且它们具有足以浮出水面的海拔。但是我们在上文(参见本章第一节,1.)注意到,当洪水泛滥时,这些山或者岛屿会与河岸边分离,看起来就像是漂流走了。所以说,这是我们分析漂浮山的观念时需要保持的一个基本观念。
我们在此也需要讨论一些相对次要的议题,比如广东漂浮稻田的传说(见本章第一节,1.)和盗贼夺走人们耕种的稻田的异事(参见前文)。通常来说,漂浮的东西都是较小的物品,比如岩石或鼓[448]。然而有一个事例很奇怪:广东沿海有一座被认为是漂浮而来的岛屿。据说某个住在会稽的人在岛上藏了一件铁器,他后来在广东发现了这件铁器[449]。因此,人们认为这个小岛原本位于会稽地区,后来才从海上漂浮到了广东。
浮邱山(漂浮小丘的山)在广东地区非常著名。这是一个小土丘,高一丈五六尺,方圆四百步,距离城西仅数里。据说它曾经像浮丘一样立在水面上,四面都有像船夫用桨划出的痕迹标。六朝时期(宋初)有百二十岁老人陈崇艺言:儿时浮浮邱山足舟船数千,山四畔篙痕宛然,今浮邱距水四里余矣[450]。我们能否认为这种故事是对于淤积和冲击沉积物延伸海岸线的记忆,这种记忆以或多或少夸张的形式保留的下来。这种情况在三角洲地区很常见,它可以解释为什么一座山会从海上漂来。
2. 浮山来自蓬莱
蓬莱是传说中的三大或五大仙岛之一,这一观念在《列子》、《史记》以及此后各种著作中都有记载。《列子》认为这些岛屿位于遥远的渤海以东,那里被认为是“北海”,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渤海湾(golfe de Petchili,译按:北太平洋黄海、渤海湾一带)[451]。《史记》中也是将它们定位在这片海域,但不是很远[452]。这部作品也告诉我们,秦始皇曾经为了找到这些岛屿前往琅琊[453]。琅琊位于山东半岛南海岸,似乎并不是前往北海之中岛屿的好地方。事实上,人们眺望东海的地方是琅琊的观景台[454]。因此,这些仙岛的位置是否变化还存在疑问。需要注意的是,在罗浮传说中,人们常说浮山就是来自于东海。
关于仙岛的最宝贵也最为古老的文本是《列子》。它最先解释了上述岛屿的方位,它们位于中国与归墟之间,归墟是陆地与天空之水交汇之处,但是那里的海平面不会因此上升(译按:八弦九野之水,天汉之流,莫不注之,而无增无减焉)。(需要注意的是漂浮山的概念和水位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无论水位是变化的还是恒定的,浮山都在那里测量水位。如果我们比较山的海拔与水位,就可以说明它们是浮动的了。)最初仙岛有五座,然而,“五山之根无所连箸,常随潮波上下往还,不得暂峙焉”。住在那里的仙圣深受其害,诉之于帝。帝恐流于西极,于是命令北海神派十五只巨鳌来载它们。只有这样,岛屿才能维持固定。但是一个巨人来到了他们所在的地方,他把鱼线一甩就钓起了六只乌龟,并且将他们还回了自己的国家。这样其中两个岛屿就失去了支撑,漂向了北极并且沉入了大海[455]。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最早的神话传说也没有排除仙岛漂流的可能性,并且确实描述了两个仙岛漂走了。17世纪末的一位学者利用钓鳌的事件解释了蓬莱漂流到罗浮山的原因:“浮山在东海中为十洲三岛[456]之一,巨鳌戴之,兀然不移也。忽而龙伯之巨人一钓而连六鳌,遂泛泛东流入于南海,与罗山合。[457]”这显然是一种文学改编,仙岛传说仅仅讲到有岛屿脱离了它们,罗浮山传说也没有具体说明浮山如何脱离蓬莱(除了它暗指尧统治时期的洪水,参见本章第一节,2.)。
安期生传记是另一个与蓬莱体系相关的传说,以下是他的传记:“安期先生者,琅琊阜乡人也。卖药于东海边,时人皆言千岁翁。秦始皇东游,请见,与语三日三夜,赐金璧度数千万。出,于阜乡亭皆置去,留书,以赤玉舄一双为报,曰:后数年求我于蓬莱山。始皇即遣使者徐市[458]、卢生[459]等数百人入海,未至蓬莱山,辄逢风波而还[460]。立祠阜乡亭海边十数处云。[461] ”我们还收集到一些关于他的其他信息,但是我们并不打算在此对他进行深入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这位仙人其实非常著名,他的名字已经进入了普遍的文学领域,例如经常使用的“浮丘公”一词。以前对于他的奉祀是在琅琊地区。而今,他在罗浮山中广为人知。晚近关于他的传记增加了以下这段情节:“齐人李少君自言,少好道,入泰山采药,修绝谷游世全身之术,道未成而病困于山林中,遇安期生,与神楼散一匕,服之即起。少君于是求给奴役师事之,遂将少君,东至赤城[462],南之罗浮,北至太行[463],西游玉门[464], 周流五岳,往返江川者,数十年。一旦告曰:我被元洲[465]召,即日当行,汝未应随我,今当舍去也。须臾有乘龙虎导数百人来迎,安期生乘羽车升天。少君遂还临淄市,寿数百岁。相传蓬莱山,三岛浮山其一也。安期生在罗浮时,尝采涧中菖蒲服之,至今故老指菖蒲涧为飞升处。《广州志》:白云山有鹤舒台,传为安期飞升处,聚龙冈北有蒲涧,涧生菖蒲一寸九节,安期生服之仙去。按:此乃郑安期,非安期生也。[466]”
罗浮山的历史学家认为这段仙传证明了罗浮山的超自然来源。为什么安期生说他要去蓬莱的时候,实际上去了罗浮?显然,那是因为在他看来,罗浮就是蓬莱左股[467]。
从我们的角度来说,这个传记反映了安期生的信仰最初是从山东开始的,之后传播到了广东地区。这可能是从琅琊地区坐船而来的移民带来的。也许我们还可以在浮山自东海漂来的传说中看到移民到来的记忆。
3. 浮山来自会稽
浮山来自会稽的传说与它来自蓬莱的传说同样历史悠久。最早提到这个观点的文献是徐道覆的《罗山记》,其中记载:“旧云浮山从会稽流来。[468]”这个文本可能晚于袁宏的《罗浮记》[469],《罗浮记》支撑蓬莱来源说。但是这并不足以断定哪个传说出现的时间更早。
会稽是一个真实的地理位置,而且非常有名,指的是位于浙江绍兴东南部的山区。该地区历史非常悠久,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随着朝代的更迭而不断变化。它的名字来源于附近的山。会稽山有多个名称,其中有一些混淆。它最重要的名字可以追溯到大禹时代的一个事件:在那里,他将王子们会集(会)起来计算(计,发音同稽)他们的功绩[470]。这也是他被埋葬的地方。我们已经知道,他也是在这里得到战胜洪水的秘方(参见本章第一节,1.)。
如果我们查看中国的总体地图,就会在海岸线附近找到会稽,大约在广州到渤海湾之间的中间位置。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古代,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中华文明是在黄河平原上形成的,随着时间推移,它的版图逐渐扩大,直到占据了我们今天所见的所有广阔领土。虽然会稽在很早的文献中就出现了,但是它直到战国时期才进入中国的势力范围,这是大约公元前5世纪,作为越国这个蛮夷国家的中心[471]。会稽是临海的,位于当时中国领地最南端。秦始皇建立帝国之后,打算巡视全境。史书记载他来到会稽,并从那里沿着海边向北行进[472]。这并不是说当时的人们不知道还有更南的地区:皇帝的军队和移民曾经在南海(广州)和象郡设置过新的郡县[473]。但是这些是非常遥远的附属地,是蛮夷之地的边境。想要到达那里非常的困难,而且只能通过山口的陆路到达[474]。在汉朝时期,中国的统治范围一直延伸到交趾(Tonkin,译按:今越南北圻,在法国殖民时期,法语名为Tonkin,东京),但是人们依然以会稽为基准衡量新领土的范围[475]。此后,会稽不可避免的失去了南部大门的特殊地位。不过,人们依然将从北边的会稽到广东以及南部更远的大部分沿海地区的国家称之为越国(或百越)。
正是由于我们在前面指出的历史原因,会稽在宗教层面上被赋予了掌管南方的地位,与衡山类似,两山一同镇守南方。所以当秦始皇踏上我们刚才提到的巡游路线时,他说:“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476]”这些仪式在理论上是持续的,它们通常带有古老的色彩。这就是为什么即使中国已经拥有了当前的疆域,在国家仪式中,依然将会稽作为南方的门户。在《隋书·礼仪志》的论述中,它被列为南镇[477]。同样的仪式还规定在会稽县界近海立祠,南海的祠则立在南海镇南(在广东地区)[478]。南山与东海相连,却与南海分离,显然这个地理认知是有偏差的。在唐代,南方的镇山依然是会稽,人们在越州(绍兴)祭祀会稽,在广东祭祀南海,而在莱州(位于山东半岛的北海岸附近)祭祀东海[479]。
这种仪式性的地理定位即使不是人为设定的,也至少是约定俗成的。虽然会稽被认为是在南方,或者更确切的说是在东南方,但是人们不会忽略它真实的地理位置是在东方。
在谈到秦始皇远征时,《淮南子》说:“丁壮丈夫,西至临洮、狄道(甘肃)[480],东至会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江西和广西)[481],北至飞狐、阳原(山西)。[482]”我们在此只对“东”字做注释:“会稽,山名也。浮石,随水高下,言不没,皆在辽西界。一说会稽山在太山下,封于太山,禅于会稽是也。[483]”这里说的会稽山应该就是我们所讨论的会稽山。有人认为“会稽或作沧海”。这个注释需要一些说明。代表中原军队前进的极点的北方、南方和西方三个方向都有两个地点,互相之间非常接近。那么,东方也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会稽距离辽西很远。我们又不可能找到另外一个会稽,但是代表东方的两个地点又确实距离很远。《史记》有一篇对应文本可以作为对照,它描述在秦始皇时期,帝国“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484],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485]”这两段文本在描述的时候带有截然不同的情绪。第一个文本哀叹“道路死人以沟量”。相反,第二个文本则是歌颂胜利。但是两者对于帝国疆域的描述大致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接纳他的观点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发现,郭璞《淮南子》注疏中提出的变体更具有说服力:他们向东至沧海与浮石(位于辽西)(译按:郭璞可能没有注过《淮南子》,但是曾引用《淮南子》注释《山海经》。)
然而,这个说法并不能让我们满意。会稽和沧海之间的混淆依然很难解释。如果文本中有“会稽”的字样,那么可能是作者或者后来的抄写者受到前后文的引导而写的。这可能上下文出现了两点:方位是东方,并且提到浮石。
在秦代,会稽并不是在中国的东部,而是在东南方。我们已经看到,相对于当时的海岸线,会稽确实很容易被划归到南方。可是文本却显示,更南方的地区当时已经被占领了。而且我们的作者生活在汉代,当时的疆域已经越过了会稽。所以,我们无法从这一点得到任何有效的结论。
我们再次回到“浮石”的问题。《山海经》(它的最终成书时间值得怀疑,但是一定不会比上述两个作品晚很多)在《南山经》一章中提供了关于会稽地区的描述。从会稽西方的句馀之山[486]开始,向东依次是浮玉之山、成山和会稽之山,其下多砆石[487]。尽管《山海经》的说法并不准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座山与浮玉山都在会稽地区。我们认为,《淮南子》中会稽山与浮石之间的联系可以通过《山海经》中会稽与浮玉山之间的联系来解释。
这座浮玉山是什么呢?我们起初很失望地发现郭璞并没有对其进行注释,但是郦道元在他的《水经注》中填补了这一空白:“《山海经》曰:浮玉之山,北望具区,苕水出于其阴,北流注于具区。谢康乐云:《山海经》浮玉之山,在句馀东五百里,便是句馀县之东山,乃应入海。句馀今在馀姚鸟道山西北,何由北望具区也,以为郭于地理甚昧矣。言洞庭南口有罗浮山,高三千六百丈,浮山东石楼下有两石鼓,叩之清越,所谓神钲者也。事备《罗浮山记》。会稽山宜直湖南,又有山阴溪水入焉。山阴西四十里有二溪,东溪广一丈九尺,冬暖夏冷;西溪广三丈五尺,冬冷夏暖。二溪北出行三里,至徐村合成一溪,广五丈馀而温凉又杂,盖《山海经》所谓苕水也。北迳罗浮山而下注于太湖,故言出其阴,入于具区也。[488]”
为了理解《水经注》的这段话,我们必须指出,这里所说的洞庭湖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位于湖南的洞庭湖,而是古太湖,也就是古具区。比郦道元更早的作者也证实了它的另外一个名字,比如震泽(3世纪末4世纪初[489])。郦道元认为《山海经》中所说的浮玉山在太湖以南不远处。所以他发现苕水流入这个湖中。然而他所提到的文本《罗浮山记》描述的无疑是广东的罗浮山,这一点可以从浮山石楼的这个细节中看出。因此,他给原本就已经混乱不堪的地理知识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混乱之处。不过他的错误只是更明显地展示了会稽与浮山(浮石、浮玉、罗浮山)的关系。
郦道元需要为他对《山海经》的解释负责,但是并不是他最先提出了罗浮山在洞庭以南的这个观点,因为他用了“言”这个字,说明他是根据前人观点而写的。我们曾经引用过5世纪上半叶的诗人谢灵运的作品,他在《罗浮赋》中解释道:“客夜梦见延陵[490]茅山,在京之东南,明日得洞经[491]所载罗浮山事,云茅山在洞庭口,南通罗浮,正与梦中意相会,遂感而作……[492]”这里确实是我们所研究的在广东的罗浮山。诗歌中提到了朱明洞天,我们知道谢灵运经常去广东地区[493]。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他不仅仅是在梦中,而是在书中读到了相关信息,这说明这种地理概念有一定的传播性[494]。
会稽山距离大海不远。我们已经提到秦始皇曾经想要登上此山观望南海(尽管他所用的这个词不一定是指海洋[495],但是古代的会稽确实拥有海岸线),这就是为什么在晚近文本中,仙岛之一的瀛洲被认为是在会稽的对面,距离海岸不远,比如《指掌图记》,甚至我们翻译过的邹师正等人的作品也有类似说法(参见第一章,1.)。这种想法在更早的时候以另外一种形式表达出来,《史记》的注疏中提到了位于东海的岛屿,秦始皇派遣徐福带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并在岛上建立了一个大型的移民聚居地。即使在今天,也有文本认为来自这个岛的人与会稽有商贸往来[496]。
考虑到仙岛传说和古代中国人对于日本岛屿的模糊认知,我们认为距离日本最近的浙江北部沿海地区是这些传说的发源地之一。
4. 结论
罗浮山传说中浮山来源的两个版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在前文说过(参见本节,2.),第二个版本并不比第一个版本更古老。但是第一种,也就是来自蓬莱的观点比第二种更著名,流传更广。无论如何,以浮山来自蓬莱为主题的诗歌数量远远超过浮山来自会稽的诗歌。我们必须承认,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才知道浮山来自会稽这个说法。相对而言,浮山来自蓬莱仙岛的这个说法则被更多的人熟知,它更引人注目,而且也更符合罗浮山的传说。但是,如果我们把会稽起源说归结为混淆了会稽附近的浮玉山和广东罗浮山,那也是非常武断的。《水经注》的作者无疑混淆了浮玉山和广东罗浮山,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他有理由这么做,他的混淆是因为当时本身就出现了糅合罗浮与会稽的传说。在我们看来,这种混淆似乎是关于广州沿海地区会稽移民历史的记忆。但是我们目前只能提出这个假设,还无法做其他的验证工作。不过,通过这种假设,我们可以把两个起源版本联合起来。蓬莱是与山东的南部沿海有关,也让人联想到远行到遥远海岸的记忆。
——————————
注释:
[448]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古代的一些浮动石头,这些石头是有声音的。在这种情况下,它必须是某种浮石(pierre ponce)。在《禹贡》中,有人说向帝王进贡了泗滨浮磬
《书经》,Couvreur翻译, p.69)。左思的《吴都赋》中也提到了浮石,并且与木筏(桴)相提并论(《文选,卷5,15a》)。注释解释说:“浮石,体虚轻浮,在海中,南海有之。”评论解释说,它们是漂浮在海上的空洞和轻质的石头。它们可以在“南海”中找到。《金楼子》 (卷5,13a,《知不足斋丛书》) 提到了以下内容: “重者应沈而有浮石之山,轻者当浮而有沈羽之水。”(这是围绕昆仑的弱水. 这个组合也见于《抱朴子》)《交州记》似乎已经引用了相同的浮石山,它位于朱崖(参见第61页,注释8):“有浮石山在海中,石虚轻可以磨脚,煮饮之止渴。”(《太平御览》,卷52,1b)另外一种浮石是龙涎香。《岭南杂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9帙,197a。越南也有一种浮岩(rochers flottants),体积与日俱增。Cf. Cadière,“ Croyances et pratiques religieuses des Annamites des environs de Hué”, II, Le culte des pierres,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BEFEO), XIX/2, p. 17, p. A 9.
[449] 《广东通志》,卷106,6b。译按:潮阳有白屿,自海浮来,后会稽人姓丁识之云会,藏铜熨斗于洲上,往取果得。
[450] 《南海县志》,卷7,6b。《广州府志》卷12,16a,中一个同类型的故事,但是是关于石头的:金鱼石大尺许,在火神庙前,相传庙前旧是大洋,石浮海面,潮不能没,今皆成田与地平矣。
[451]《列子》,卷5,Wieger翻译,p.131.
[452] 《史记》,卷28,5a;Chavann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t. III, p. 364. 关于仙岛的问题,参见Sugimoto N. et Mitarai M., Shên-shan (Divine Mountains) and Kuei-hsii (Bottomless Valley). (En japonais, résumé en anglais), in Tôhôgaku Ronshù, n° 2, mars 1954, p.63-84.
[453] 《史记》,卷6,8a。Chavann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t. II, p. 190.
[454] 《吴越春秋》,《四部丛刊》版,卷10,23a,关于琅琊台,参见Chavann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t. II, p. 144, п. 1.
[455]《列子》, 卷5,Wieger 翻译,p. 133.
[456] 三岛就是常见的三个仙岛,十洲是东方朔在《十洲记》中描述的。
[457] LFHP,卷10,24b。
[458] 关于徐市,参见Chavann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t. II, p. 190.
[459] 卢生,可能是《淮南子》中提到的卢敖。
[460] 《史记》,卷28,11b,百衲本。Chavann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t. 111. p.437.
[461] 《列仙传》,《道藏》,14b-15a。(Wieger, Canon taoïste, n° 291. Voir Pelliot, JA, 1912, p.149)
[462] 赤城是在浙江的天台。十大洞天之六。
[463] 太行,古代名山,位于山西。
[464] 玉门,或称玉门关,位于甘肃,靠近敦煌。
[465] 元洲或玄洲,《十洲记》的十洲之一。
[466] LFHP,卷4,1b-9a。
[467] 《浮山纪胜》,《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4帙,461a。
[468] 徐道覆,《罗山记》,《太平寰宇记》,卷261,3b。
[469] 《元和志》,卷34。
[470] 《吴越春秋》,卷6,8a。Chavann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I. I, p. 171, t. II, p. 132, n. 1.
[471] 《史记》,卷41,1a。《吴越春秋》,卷3。
[472] 《史记》,卷6,11b。Chavann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t. II, p. 184-186.
[473] 同上,卷6,9b。Chavannes, op. cit., t. Il, p. 168. Sur la commanderie do Siang. cf. H. Masporo, BEFEO, XVI/ 1, p.49-55 ; R.A. Stein, Le Lin-yi, p.202-208.
[474] Cf. L. Aurousseau. “La première conquête des pays annamites”, BEFEO, XXIII, p. 145 suiv.
[475] 参见《通典》,卷185,45b(鸿宝书局);《前汉书》,卷28b,16b,服虔的注释(3世纪末以前),其他注释者混淆了它们。
[476] 《史记》,卷6,11b,Chavann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t. II, p. 186.
[477] 开皇十四年的诏书,《隋书》,卷7,7b。
[478] 南海镇的这个表述并不清楚,南海当时是郡(commanderie),不是驻地(garnison)或者市井(marché),镇这个字也有固定的山的意思,但是人们没有说这个山是什么。
[479] 《通典》,卷46,60b,《前唐书》,卷24,1a。《新唐书》,卷15,6b。
[480] 临洮是长城的起点(参加《史记》,卷88,1a,蒙恬列传),因此这是一个流放的地方,罪人被流放于劳作(《史记》,卷6,2a)。狄道也在这一地区,目前仍有以此命名的县。
[481] 飞狐位于山西,是泰山以南的一座山。阳原是当地的一个县。这段话见于《淮南子》,卷13,8a。
[482] 所用的 "裨 "字肯定是 "禅 "的错误。校按:本条注释没有“禅”字,禅字在下一条。
[483] 《淮南子》说:“尚古之王,封于泰山,禅于梁父。”(《淮南子》,卷11,8b)。古代所有圣王中,只有一个人是禅会稽,就是治水的大禹(参见《史记》,卷28,3a)。
[484] Cf. R. A. Stein, Le Lin-yi, p. 124-126.
[485] 《史记》,卷6,6a;Chavann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t. II, p. 135-137.
[486] 郭璞的注释认为这座山位于馀姚县之南,句余之北,更确切的说是句章之北(参见《后汉书》,卷3a,3b,引用的内容与郭璞的注释相同。另参见《水经注》,卷29,11a)。现代学者认为它位于宁波地区(毕沅,《山海经校证》,根据《元丰九域志》),或者面向湖州,也就是太湖以南(相同的注释见于《太平寰宇记》)。
[487] 《山海经笺疏》,卷1,8a。
[488] 《水经注》,卷29,6b-7a。
[489] 《文选》,卷5,32b-33a:两句平行的句子提到,一个是包山(或苞山),这是洞庭山的名字,另一个是洞庭湖的名字。注释引用了晋代《扬州记》说“太湖亦名洞庭”还有一部图记中说 “太湖中有苞山”。现代的地图显示,在太湖分别有东西两座洞庭山。
[490] 延陵是晋代的一个县,位于现在的江苏的丹阳以南。现代地图上,茅山位于这两个城市之间,位于连通太湖的支流的西部。
[491] “洞经”一词难以判断是指道教经典,还是某个标题中有这个词的书籍。
[492] LFHP,卷14,1a。这篇赋被保存在《异闻集续》,卷7,29b,这篇文章也被抄录在《北堂书钞》,卷158, 26a。
[493] 他在晚年被流放至此。参见《宋书》,卷67,14a。
[494] 有人可能会反对这种观点,茅山既不是洞庭也不是会稽。这确实是事实。但是只有茅山是延陵茅山时才是如此。从古籍中,我们可以看到,会稽的古名是茅山(《吴越春秋》,卷6,10a:遂更名茅山曰会稽之山;《越绝书》,卷8,1a;《水经注》,卷10,11b:又有会稽之山,古防山也,亦谓之为茅山。《史记》,卷28,3a,索引与正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南方的罗浮山(以及其他方向的地方)的沟通,既来自于太湖的洞庭山,也来自于茅山。
[495] 四海是指疆域之外的地方。参见M. Granet, La pensée chinoise, p. 92 ; Wang Yong 王庸. “Seu-hai ťong-k’ao 四海通考”, in Journal of History and Geography, n° 2, juillet. 1927.
[496] 《史记》,卷6,8a。《正义》,引《括地志》。7世纪的作品,同一篇论述中还引用了《外国图》,这是一个来自其他国家的表格,由吴国的一个人制作,根据该图,这个岛屿距离琅琊的海岸有万里。校按:“吴人《外国图》云:亶洲去琅琊万里。”原文:“《正义》:《括地志》云:亶洲在东海中,秦始皇使徐福将童男女入海求仙人,止在此州,共数万家。至今洲上人有至会稽市易者。”

苏远鸣(Michel Soymié,1924-2002),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讲席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宗教与文献,涉及民间宝卷、佛道关系等主题,尤其在整理伯希和所藏敦煌文献方面贡献巨大。

张琬容,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远东研究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集中于道教与民间信仰,法国汉学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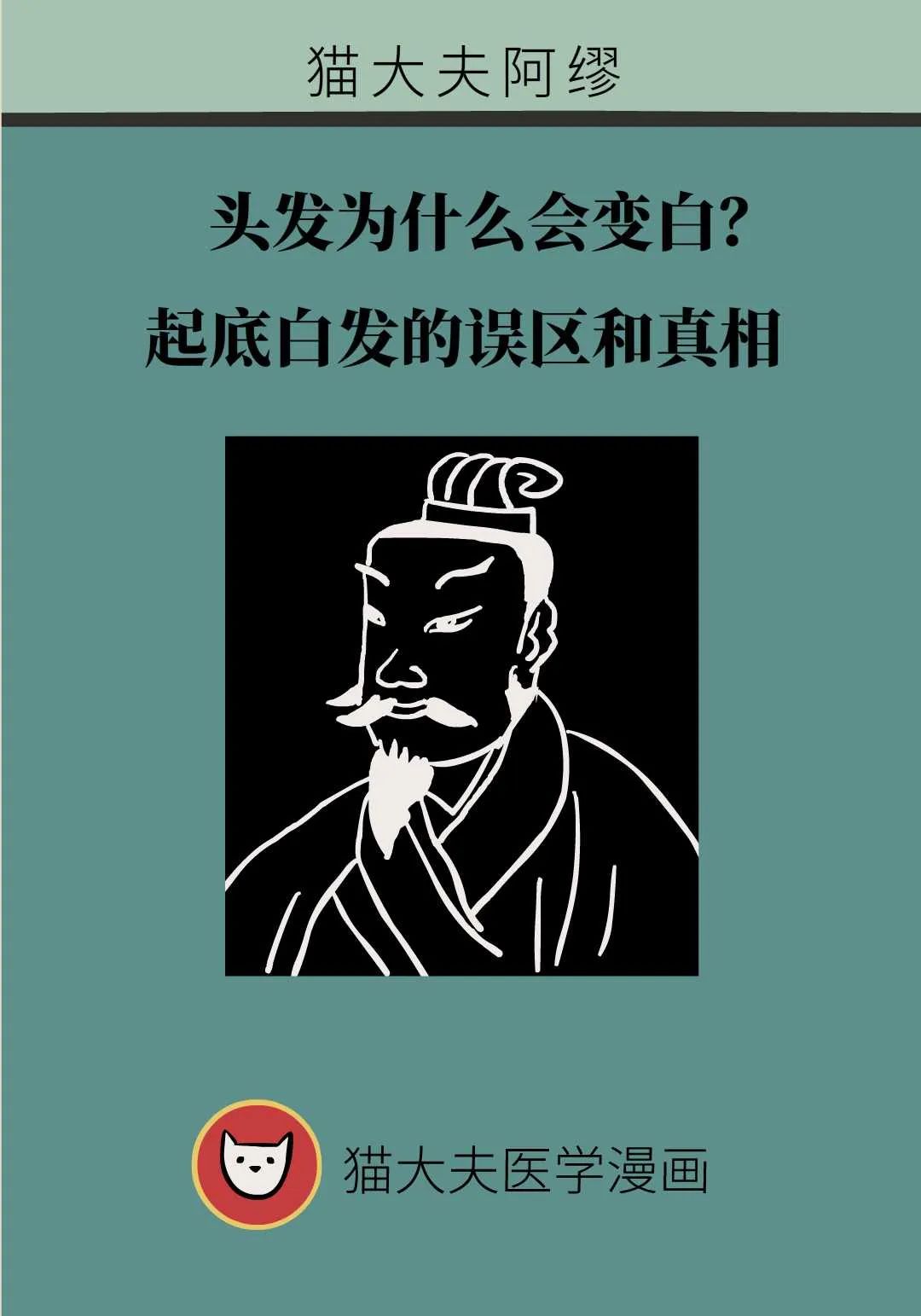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
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 京ICP备11000001号
京ICP备1100000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