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家人逛一古镇,吃到了一家很不错的酸菜鱼。古镇里的餐馆多同质化,想找到味道独特的美食,不算容易。
已过了晚餐高峰,老板娘在厨间收拾,老板倒了酒,整了菜,一个人小饮起来。在繁华的商业街上,这个中年男人有点“红尘隐者”的意思。
酸菜鱼的味道好,我们给老板点赞,他酒意上脸,倒也不过谦,回一句:“食材正,烧鱼有绝活,这样的酸菜鱼才立得住。”
听说有绝活,我当然要寻根问底。老板虽操着一口普通话,却有点“夹生”。我年轻时和很多四川人要好,能从他的口音中听出一股“川音”。问他老家哪里,果然是四川。
他从小兄弟姐妹多,父母负担重。十五六岁就不再念书,到社会上闯荡。最苦的时候,在街上打过地铺,连坟地都睡过。但他一点也不怕,从没有向生活认输的念头。他跌跌撞撞,各种打工,各种碰壁,各种辛酸,直到做起掌柜来。
他说:“你们可别嫌弃我话多。”我告诉他,不会的,我爱和有故事的人聊天。他颇为受用地笑了,把手中的酒一饮而尽。
他和我年纪相仿,但他像是老幺,家乡的白发老母想必已经八十开外了。多年来,他生意做了好些种,最后在这个小小的古镇上卖起酸菜鱼。铺子楼上楼下,租金倒也不便宜。每年算下来也没挣到大钱,但好在“年年有鱼”,这就知足了。
他自嘲自己是伙计,给老婆打工。老板娘听了这话,回头淡淡一笑。
这世上最质朴的爱情,就是这般“一起开店,一起做鱼”吧。
我见过他烧鱼的样子,干练、简明、悦然,一气呵成。这套做鱼的法则,像是每天必走的套路,但灵魂正是他所言的“绝活”。其实,“绝活”就是他小时从母亲那里“看会”的做酸菜鱼的要诀。从片鱼、腌制、勾芡到入汤、出锅,样样透着机巧。
“我离家时还小,我母亲并没有悉心传授我什么做鱼的技法,很多细节是我日后想起来的,有些诀窍是我在漂泊的日子里悟出来的。如果说我母亲教过我,那就是她说过的不怕吃苦、跌倒了再爬起。”
他说来说去,我给总结为“母亲的味道”。他点头称许。
在这离家几千里的江南小镇,一个中年汉子,用一锅酸菜鱼“立住”了自己,养活了全家人,给了母亲莫大的安慰。
人做些什么事,抑或操持何种生意,很多时候是机缘巧合,但细细想来,一门生意、一种活法,都有源头。若不是少小离家,想念母亲而不得见;若不是平日里吃遍地方食物,依恋故乡水土而不得近,他会不会“贪吃”酸菜鱼成瘾、会不会突发念想以做鱼为谋生手段?
我没有问他,但我知道,酸菜鱼这个意象,是与生俱来的,是命运的赐予。“绝活”用与不用,都在那儿。
我听不少来自外乡的餐馆老板说过,做吃喝生意,比起其他的,稍微有些把握。虽说众口难调,但若有“绝活”支撑,生意就成功了一半。
我曾在一家土菜馆尝过香肠,味道大赞。老板自豪地告诉我,是按照老家母亲的“土法”腌制的,那是“母亲的味道”。
从前,我也是游子时,只知道“母亲的味道”是用来慰藉乡愁的——这种感觉就如同“酸菜鱼老板”在讲述往事、提及母亲时的一脸陶醉。可人到中年,我才知道,“母亲的味道”也可以是帮助自己自立于人世的一柄“利器”。
这样的利器,无鞘无利刃,却有着取之不尽的机巧和力道。它一再提醒离开母亲出外打拼的人,一个人不忘母亲只是本分,从血脉的源头学到本事和恒心,才是人生的要务。
这样的味道,这样的执念,会长存于世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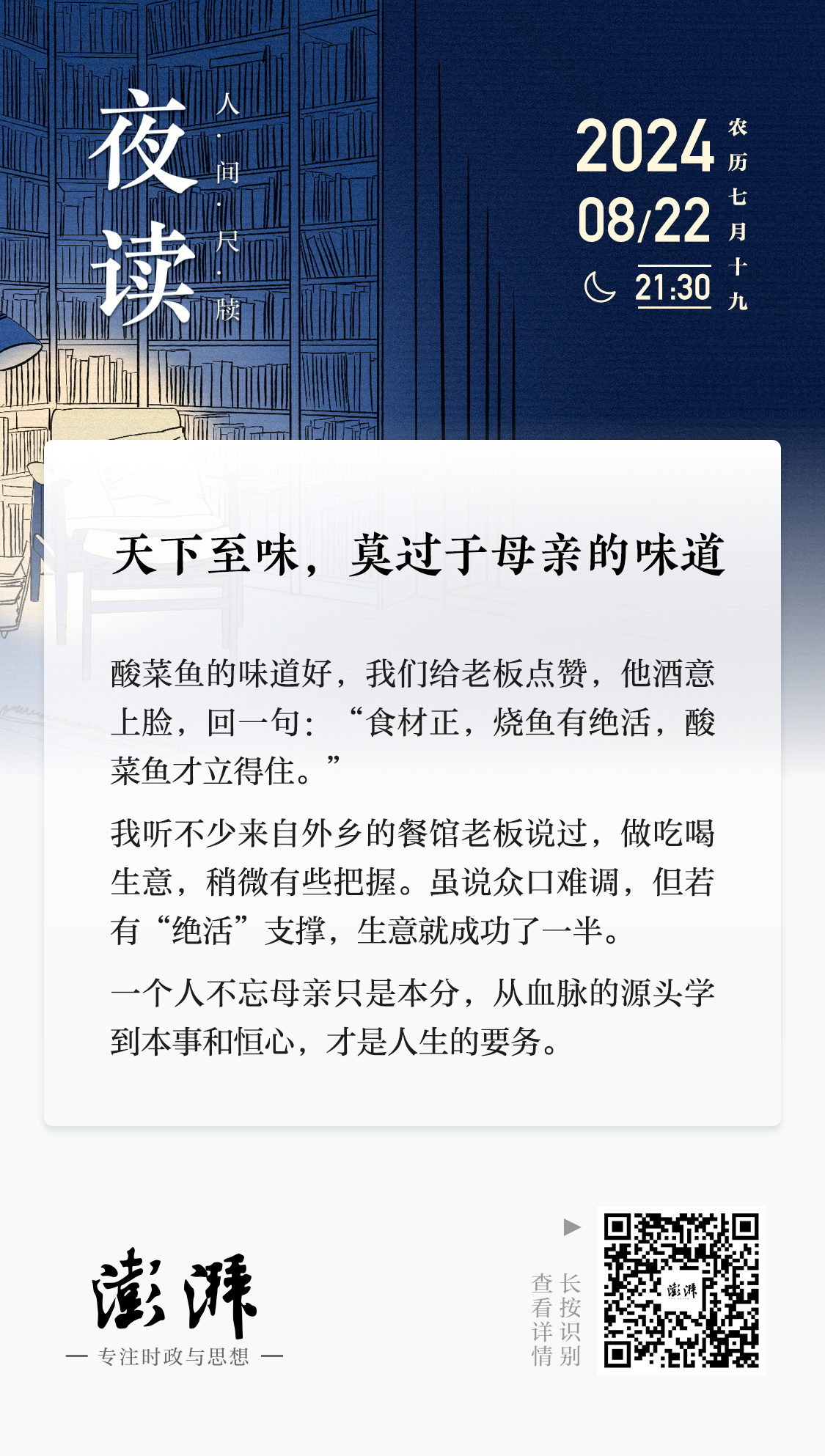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
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 京ICP备11000001号
京ICP备11000001号